
读创文化2022/11/27 00:4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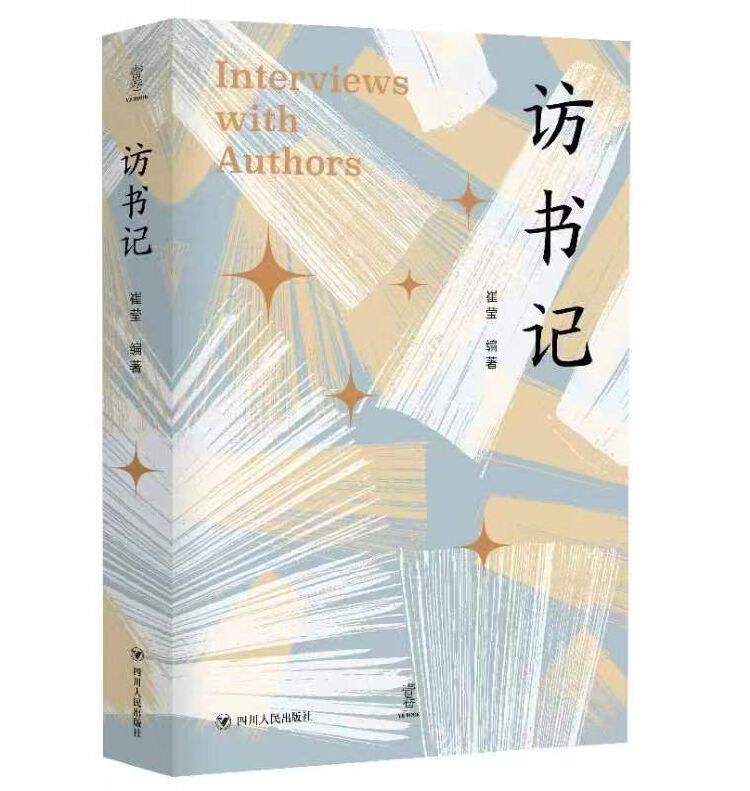
甫一接到崔莹写的这本《访书记》,立马被精巧的封面和厚重的内容所打动。这本书的英文译名倒更符合全书的主旨——“InterviewswithAuthors”,窃以为应命名为“名家访谈录”。然而,这并不影响此书带给读者的乐趣。从汉学到世界史,从文学到非虚构,从社会学到流行文化……在我们这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年代,博学洽闻的崔莹博士不仅真诚地“拥抱了所写的文字”,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广阔的东西方精神世界的模样。
这本书虽涉及人文社科诸多门类,但是一本所有人文科学爱好者都感兴趣的著作。对未曾读过书中所列书籍的读者来说,本书提供了作者本人对其作品的反思,是吸引读者进一步了解和阅读的敲门砖。对熟悉书中所提书籍的读者来说,本书更是一本不可或缺的补充读本。一反罗兰·巴特所言“作者已死”之论,此书强调了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与作者的反思。这并不是鼓励我们将作者的诠释奉为圭臬,甚至限制了我们对原有作品的想象。相反,崔莹博士与作者们的一问一答给予了读者更多维度的思考方式。更何况,一部作品的诞生,必然离不开作者自身的成长经验和社会环境。诚如鲍曼在书中访谈所言:“我是齐格蒙·鲍曼,我写的也是齐格蒙·鲍曼的想法,齐格蒙·鲍曼的想法受在波兰生活40多年的影响,也受在英国生活40多年的影响。”
本书所有访谈被分为六个主题。作为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,我首先关注的自然是“社会学”板块。虽然只有齐格蒙·鲍曼一人的访谈被列入其中,但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,至少彼得·伯克关于年鉴学派的讨论,以及阿什利·米尔斯从性别政治角度对模特行业的反思,都可被归类为社会学的讨论范畴。当然,书中的分类也无可厚非。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学本身就有众多分支,能与其他人文学科组成交叉学科,很多著作自然也可被分类到历史、文学或非虚构文学、流行文化等领域。另一方面,鲍曼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学学者。他虽然一生只专注从事过社会学家这一职业,但他始终紧跟潮流,所著书籍涉猎社会学、哲学、媒介传播、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等,也难怪单独为他安排一个主题。
鲍曼是我非常喜欢和欣赏的社会学家。即使九十高龄,仍然每天四点起床,一生笔耕不辍,敏锐地对当代社会提出颇具原创性的见解。与推崇后现代思想的让·鲍德里亚、德勒兹、詹明信等理论家不同,鲍曼完成了从他早期所认同的“后现代性”到晚期使用“流动的现代性”的转变。他坚定地认为,我们的时代仍然属于现代,然而这个“现代”是不断变化的,是无止尽的“现代化”过程。这种哲学思想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人的自我构建与危机处理。人们不再喜欢一成不变的事物,而是上瘾似的投入“现代化”的改造中。
崔莹博士询问了鲍曼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可能最感兴趣的问题,例如“社会学的作用是什么?”“社会学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快乐么?”鲍曼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:“社会学的职责是在变化的世界中提供一个方向,这个职责也只有在跟踪这些变化及其结果,以及研究和思考人们针对变化所采取的对策中实现。我相信这个世界永远都需要方向,这也是社会学在探求和给予的。”对他而言,社会学家应该作为社会的观察者与建言者,为一个更好的社会出谋划策。同时,他也认为社会学家不应成为政客的附庸,更要站在大众的一侧,“对付由当权者带来的这些糟糕之处”。我认为这可以当作对所有社会学者的警醒: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应当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,不仅是对社会,也是对自己。
而关于第二个问题“社会学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快乐么?”鲍曼给出了让我略感惊讶的回答。他毫不含糊地回答“可以。”并且进一步说:“如果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变化,以及这个世界如何影响我们,人们会变得更快乐。”这就是九十高龄的社会学家的豁达感悟。
在我求学过程中,身边的同学甚至自己都会常常陷入“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,还是快乐的猪”的难题。因为当接触了性别研究、权力关系等批判理论,再看到庞大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限制,就容易产生沉重的无力感。然而,鲍曼在此告诉我们,成为“快乐的苏格拉底”是完全可行的。与其选择充耳不闻,不如在不确定的流动现代性中保持思想的清明(self-clarification)。
另一位社会学界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便是布罗代尔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研读过布罗代尔的“长时段”理论。然而,彼得·伯克在访谈中告诉我们,即使作为学派中的元老级人物,布罗代尔认为自己是异端。因此,《法国史学革命》着眼的是年鉴学派的整个群体,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学派领导人。令我惊喜的是,这篇访谈也凸显了本书重视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宗旨。在访谈的末尾,彼得·伯克表示汉学家卜正民和伊懋受年鉴学派启发很大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可以在崔莹博士与卜正民的访谈中窥出端倪。卜正民表示,在书写《哈佛中国史》系列的《挣扎的的帝国:元与明》时,他创新性地从环境历史的角度分析明朝没落的原因,这与布罗代尔强调历史地理结构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。书中的这些遥相呼应与隔空对话,是阅读时的额外乐趣。
放眼其他主题,贯穿全书要义的,是全球主义的关怀,以及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主导叙述(masternarratives)的迷思。白馥兰在访谈中直言:“‘李约瑟’”难题是伪命题。”因为它预设了以西方的文明和技术为标准的欧洲中心主义,而忽视了非欧洲人的成就。同样的,薛凤也指出,写出《天工开物》的宋应星“并未创造西方已有的东西,他独一无二的创造缘于明朝的中国世界,他对工艺的解读也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思想。”从崔莹博士与这些汉学家的对话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致力于让西方民众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,并且搭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。如卜正民所说:“我写这四本书,都缘于我希望了解中国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。”要破除克里斯多夫·弗雷林所言的西方“恐华症(Chinaphobia)”印象,我们亟需更多类似的作品,以及国内外优秀的引介。
虽然汉学占了较多篇幅,本书并不囿于中西方的对话。它也包含了后殖民主义的讨论,以及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处境。例如坚持用母语吉库尤语进行写作的恩古吉·瓦·提安哥,认为语言就是身份政治最直接的展现,因此他至今仍然使用母语进行文化抵抗。获得英国布克奖的美国黑人作家保罗·比第没有选择对种族问题进行脸谱化的呈现,他在访谈中强调:“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简单的‘黑’与‘白’。”“我希望我的作品让人们明白:世界上存在很多灰色地带,有很多矛盾、很多虚伪。”无独有偶,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阮清越也提到:“对于少数族裔,对于来自曾被殖民国家的人而言,过去的历史和文化都是苦涩的幸运。战争、殖民……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塑造我们的历史,即使我们知道它们不应该发生,但也正是这些不公正的苦涩历史塑造了现在的我们。”对他而言,东方与西方、自我与他者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。我们从本书的很多访谈中看到,在文化混杂性(culturalhybridity)下,后殖民作者们如何在种族与普遍性的两难境地中抉择。这不禁让我想到后殖民理论家弗朗兹·法农在《黑皮肤,白面具》的末尾所说的:“我不是那使我父祖成为非人的奴隶制度的奴隶。历史的厚重不会决定我的任何行动。我是我自己的根据。只有当我超越历史的、工具的事实时,我才导入我的自由进程。”阅读这些作品与访谈,对读者了解鲜活的南方(theGlobalSouth)境况以及后殖民国家矛盾的多重交织性有着极大帮助。
当然,除了以上关于书籍内容的严肃讨论外,总共51篇的访谈也包括了著作诞生的幕后故事与写作的经验之谈。对热爱阅读与写作的读者来说,这些内容能带来诸多启发。与随身携带纸笔记录灵感的作家不同,《小报戏梦》的作者罗伯特·奥伦·巴特勒则认为:“作品不是通过分析诞生的,而是从潜意识中诞生的,从作者的经验中发酵分解而来。”对他而言,从每个人的经历中自然生成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吸引力。两获布克奖的希拉里·曼特尔在撰写“克伦威尔三部曲”时选择绝对尊重历史事实,表示:“真实发生的历史比我的创作更精彩,即使事实很乏味,我也不会改编历史,只会调整我的叙述方式。”除了这些文学作品外,翻译作品也属于一种特殊的原创。在与花费12年译完《易经》的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的访谈中,他强调了传统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三原则之外的第四原则“化”,即“译者要能够在重铸、重塑、重组文稿等诸方面下功夫”。这个说法挑战了杨绛先生所言的“一仆二主”(译者作为仆人,伺候着两个主人:一是原著,二是读者)。对闵福德来说,译者要将自身主体性与作品深切融合,如此才能完成不违原著且富有感情的创作。这样的经验分享不胜枚举,由于篇幅所限,恕不能一一所列。若仔细品味,对读者而言定能收获颇丰。
崔莹博士不仅博览群书,而且还利用她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以及长期旅居海外的优势,给我们献上了琳琅满目的阅读盛宴。在感受谈话的思想碰撞时,相信每位读者都能拥有醍醐灌顶的喜悦感,甚至“阿基米德时刻”。
作者:赵嶷如 (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)
审读:喻方华

读创首席编辑
李琰